他刚刚抵达曼彻斯特,为了 The Warehouse Project 的一场门票业已售罄的个人演出。但 Michael Bibi 的心思却在这座城市稍早些的另一场演出上。是他去年3月,在 Joshua Brooks 的巡演专场吗?“不是那场,”他告诉我们,他那黝黑、年轻的面庞被一绺深色刘海衬托着。
让他记忆犹新的活动是在2016年12月,在小型地下室俱乐部 Stage & Radio,参加 Bibi 的俱乐部之夜活动 Solid Grooves 的人一度填满了伦敦的1500人的场地。曼彻斯特是 Bibi 在首都以外第一个预定的城市。“我已经计划了很久,我以为会很精彩,”他说着,脱下了外套,露出一套全黑的工装裤和 Balenciaga 卫衣。“我去了那儿,就10个人,最多也就10个了。那着实是迅猛、教人清醒的一击——‘不,伙计,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靠在酒店房间的沙发上的他说到。
在2019年10月,当他单枪匹马地将足以容纳3000人的伦敦场地 Magazine 的活动门票售光之时,Bibi 看上去就像是凭空出现的成熟 DJ,但在那个职业生涯的决定性时刻,与令人失望的第一场曼彻斯特演出之间,发生了许多事。
在经营了六年夜晚兼俱乐部的唱片公司 Solid Grooves 后,2018年夏天,Bibi 制作了《Hanging Tree》,这首催眠式的歌曲,是他在电影院看《饥饿游戏》时偶然冒出它的小样的。由于他专注于自己唱片公司中的其他艺人,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让唱片公司获得成功,他忘记了这首歌。直至三年后,正在制作的一首重混音作品才让他想起它。他在45分钟内把它完成,并在当晚 Egg London 的演出中播放了它——这首歌迅速火爆了。
继而开始的一系列活动令 Bibi 蹿升为 DJ 巨星——15秒内售罄伦敦 Leake Street Tunnel 的演出票,一举夺得2019年 DJ 奖(DJ Awards)的“最佳 Tech House DJ”。并在 Privilege Ibiza 举办了非常成功的 Solid Grooves 驻场活动。
他现在觉得自己出名了吗?
“我觉得被接受了,”Bibi 用因经常旅行而被淡化了的伦敦口音答到。在我们会面时,他上路已有六个星期,短期内也没有放缓的迹象。
今年夏天(COVID-19爆发之前),他已经被预定与 Jamie Jones、Adam Beyer 、The Black Madonna 一道,参加 Amnesia 的开幕派对。担任巴塞罗那 Offweek 音乐节 Solid Grooves 舞台的负责人,再回到曼彻斯特参加 Parklife 音乐节等无数场演出。
“直到最近,我才觉得自己被音乐行业接受了。”他描述道,在父亲的建议下,他勉强地完成了为期三年的电气工程课程。之后,他离开了伦敦的 rave 现场,正是在那里,他爱上了drum’n’bass,和在 Fabric 举办的 True Playaz(由 DJ Hype、DJ Zinc 和 Pascal 共同经营的 drum’n’bass 和 Jungle 风格的唱片公司)之夜。之后去了东南亚旅行。
就是在这一年的假期,迷上 minimal house 的他,决定成为一名 DJ。但是,当他回到伦敦时,现实给了他一击:在这个行业里,他谁也不认识。挨门挨户地去寻求演出机会,在他被布里克斯顿的场地拒绝了个遍后,终于说服了 Jamm 给了他一个机会。感谢他在 rave 现场里的朋友,助他填满了俱乐部的场地,并且这在后来成为了他的标签:长久且不懈地推广。
2014年转向制作时,他再次遭到拒绝。“还是那句话:‘不,不,你是谁?这音乐很怪’”——不过,出于宽厚,他不会点名道姓地提及任何唱片公司。他之所以坚持不懈,他说,是因为“当我有了想要做某件事的想法时,我就会顽强地坚持下去;我从来没放弃过,所以我就想,‘我不会放弃的。’”
Michael 想被接纳的渴望可以追溯到他的音乐生涯之前。“刚上中学的那几年,我很笨拙,并不合群,”他承认道。他耸肩时,银色的戒指和项链让人眼前一亮。“但当我把混音作品集合在一起时,我发现——我过去常常做混音合集,然后就把它们发出去——这样做会是一种让我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
音乐会改变人们对你的看法的认识,这是他的切身体会。
那时的 Bibi 10岁,和父母一起住在温布尔登,学习着弹吉他。“我必需要做一首一级的古典音乐作品,我拿了满分。”他回忆道: “这在那个年龄是闻所未闻的,我记得那种得到尊重,或是钦佩的独特感觉:因为我做了这样的事,人们就认识了我是谁。”
他拉着连帽衫的抽绳,更为加重了他的羞涩感。间或会出现轻微地社交上的尴尬——眼神交流中断,摆弄他的衣服,或者从他通常自信的举止、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轻松温暖的姿态中稍稍转变,这让人想起了他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童年记忆。
Bibi 的基因里就有着音乐天赋。他的父亲是布鲁斯吉他手 Robin Bibi,曾与 Robert Plant 和 Ben E King 等人一起合作,他的母亲是舞蹈老师。他的弟弟也同样拥有音乐天赋,但他决定成为一名厨师。
“我的弟弟通常更像我母亲,而我更像父亲,”Bibi 说。虽然他的父母在他接触电子音乐(他父亲称之为 “锅碗瓢盆”)的时候,起初并不太高兴,但他父亲的布鲁斯唱片——从 Skream 和 Benga,到 Felix da Housecat、Jamie Jones 和 Lee Foss等一系列的广泛影响,最终形成了 Bibi 的音乐。
“很多布鲁斯歌曲都很有深度。至于歌词,你几乎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声线听起来却非常的很懒散、很邋遢,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点,”他说。提及 Doc Watson 和 Roscoe Holcomb,“我觉得我很多作品——《Got The Fire》、《Devil’s Candy》——它们都很缓慢、很慵懒,如果你听布鲁斯歌曲,布鲁斯歌手的歌,你就会发现,我与他们的风格非常相似。”
采样也是 Bibi 音乐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对那些晦涩而诡异的声音很敏感,例如他2019年发布的作品《Groove Garden》。
“我对什么都会采样,”他说,“在我的工作室里,我从来没用过什么硬件。我只有一架 Moog Minitaur(一种小型低音合成器)和一台罗兰 TR-8 鼓机,这还是我在八个月前才有的。在那之前,都是用软件——只有我,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但在 Bibi 过往的许多作品里,采样都处于次要地位。他将自己的创作过程描述为速度至上。他说:“如果我有一个想法,我必须在一个小时内把它做出来,过了这个小时的话,我的大脑就不再活跃了。”
他的方法与现今音乐制作和发行的快节奏相一致。“我曾花很长时间去寻找适合我作品的采样,这让我失去了那种流畅感,所以我想,‘让我录一下我自己的声音,就现在’。但我把录音放上去,然后我觉得,‘只用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错’。”
这并不是说,Bibi 不是一个执着于彻底贯彻的人:“如果我要发表一首作品,我会对它做很多调整,之后再回到第一个版本。我总是发现,你只有在尝试过所有的东西之后,才知道这些你都不想要。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舒服。”
说到做 DJ,Bibi 灵感主要来自于他多年来的狂欢,正是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关于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以及人们想要的氛围。”
他那标志性的克制手法——没有大幅地下降, 但稳定的BPM 被爵士和拉丁风味的点缀所穿透, 同时通过朋友和唱片公司同侪的作品来保持对 tech-house 的承诺——这一点在他的混音中得到了证明,比如他在 Tobacco Dock 的 set,以及当晚后来他在 The Warehouse Project 演出。这种独特的风格,辅以天生的直觉,与 Bibi 精心设计的职业生涯相辅相成。
他说,在他推广的那些年——定一个凌晨3点的闹钟,然后去俱乐部外发传单。让他在《Hanging Tree》大获成功之后,不顾经纪人的建议,大胆地制定了一场个人巡演。
他解释说,他可以摘下艺术家的帽子,戴上推广人的帽子,去询问:“Michael Bibi 在这个城市能卖出多少张票?”他发誓再也不要只对着10个人演出,这促使他对自己粉丝的标准和定位有了更透彻深入的了解。这也导致了他的巡演场场爆满,甚至引发了更多的炒作。
Bibi 对长达四、五个小时 set 的热情,来自他个人精神解脱时的一次觉醒。在2019年初的巡回演出中,他为自己取得的新成就的高度所兴奋,他对一切都说‘是的’:“每一次演出后,每一次活动,继续向前,向前,向前,”他回忆道,在利兹大学的学生宿舍,他的一次难忘的演出。当时有很多人挤在客厅里,地板都差点塌陷了。周遭一片混乱,Bibi 一直在台上放到了中午。
他童年时代遗留下的——结交朋友、取悦他人、被人接受的渴望——正威胁着他,要把他燃尽。他同意道,但也指明他了解自我的诀窍,比任何人都来得有效,并说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他向经纪人请假,去牙买加参加冥想和瑜伽静修——只有他、另外一个人和瑜伽老师,在那里,24小时见不到人稀疏平常。
他承认说:“当时我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这是我一直想要达到的高度,但也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不快乐的时候。”他完成了这个计划——果汁排毒、数字排毒(远离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以为自己减压或将关注点转移到真实世界的社交活动中)和大量的冥想——但随后他又直接回到了音乐创作上,在旅途余下的时间里,他都是在笔记本电脑上来创作的,包括2019年6月的作品《Isolate Ctrl》。“我又回到了最初,那时我做音乐只是为了兴趣,只是为了爱,”他笑着回忆说。
至关重要的是,他也逐渐意识到,对他来说,冥想有助于达成泡俱乐部的目的。“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去俱乐部,又和你的朋友一起离开。但当你跳舞的高峰时刻,你正处于自己的巅峰状态,你越是将自己孤立起来,你就越能全情享受它,”他说,解释到这种认识启发了“Isolate”,这一他回归后提出的俱乐部的概念:只有他自己,玩上一整夜。焦点和音乐的统一,旨在创造一个冥想的状态。
“我觉得很多 rave 文化都体现在你的手机和其他东西上。这很棒,但你要记住,要与自己保持连结,我觉得真的可以通过狂欢来了解你自己。”
我们很想看看这一概念在一个水泄不通的俱乐部里是如何运作的。当然,在 The Warehouse Project 的 Concourse 舞台上,当一场能容纳10000人的 Mayfield 场地上的演出票被售罄时,在身体上隔离自己还是有些困难的。
确实如此,即便在 Bibi 抵达之前,观众看上去就已更像是一片躯体的海洋,而不是清晰可辨的面孔了。当他在午夜登台时,气氛瞬间发生了变化,全场的兴奋之情已溢于言表,“Bibi,Bibi,Bibi,”尽管外面下着无情的大雨,但热爱跳舞的人们还是身穿短裤和T恤来了。他们高呼着,当一个圆形的光环雕塑悬挂在上空:Isolate 的 logo。与此同时,红色的激光照射在废弃的火车仓库的钢柱上,散逸着温暖的光芒,让观众的墨镜也不再觉得格格不入了。
很快,Bibi 略显瘦弱的身材在舞台上显得更有气势——双臂经常横展于三个平台,让他的观众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很难找到一位不紧盯着圆型舞台的狂欢者,这舞台位于地面上,让人联想到圆形剧场。
Bibi 认为俱乐部音乐可以成为一种冥想方式的想法,在他开始穿插一些歌曲片段,就像转瞬即逝的思绪之时,才得以实现。歌曲涉及的范围很广,在诸如 Sophie Ellis-Bextor 的《Murder On The Dancefloor》、 Dizzee Rascal 的《I Luv U》和 Gorillaz 的《Feel Good Inc》等曲目间,萦回着、挑逗着,但从未完全取代那令人舒适的重复节拍。当 Bibi 表演自己的曲目时,他就成了 tech-house 的 Billie Eilish(2016年因首支单曲走红,被誉为“全球超级新人”的女歌手),向着无归属感的 Z 世代*,低语着他的悲伤旋律。
*Z世代一般指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情感上普遍孤独,正处于价值观“自我认知”与“群体认同”的关键时期,比任何一代人更加频繁地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等媒介来传递、获取信息,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他们的独特的审美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
鉴于他的粉丝们在 The Warehouse Project 上表现出的虔诚——他们的手紧紧抓着隔着透明玻璃的隔板,当他到来时,不计其数拍摄他的手机点亮了整个房间。他播放完最后一曲,伴着如潮的掌声,数十位粉丝要求与他自拍——我们想知道,自他第一次有了这个主意起,他是否后悔没能早点把《Hanging Tree》制作出来。
“不,”Bibi 带着深思熟虑后的肯定回答道。“每一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中,都会有一个催化剂,让你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把你推上风口浪尖,每个人都会问:‘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得到那个催化剂的时刻,我想,当聚光灯降临到你头上时,当人们开始问,‘Michael Bibi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大量的作品储备。”
至于这些以探寻、忧郁的人声为特点的作品,可以追溯到他父亲的那些蓝调唱片,这也许是他能在这个时候找到如此多的听众的原因,这些曲目符合时代潮流。但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坚持不懈,以及他在这个行业各方面的广泛经验,也意味着他能够精确地执行每一步。
尽管如此,当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及成名的想法时,他还是动摇了。“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出名,”他说;然后又停顿了一下,承认我们可能说到点子上了。他回忆起近期在阿根廷的一场派对之后,迎接他的欢呼声震耳欲聋,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是的,这可能是我接下来要确保自己要保持住的东西了,”他说。
“不过,我依然很普通,”他想让我们知道,于是他热情地与我们拥抱告别——这是一位超级巨星,但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抛除所有的成就,有时的他,依然还是校园里那个试图交到朋友的害羞男孩。
// 翻译:topazz
编辑:Jack
有关文章

Mixmag|从街头到赛场:电子音乐竞技的历程
Mixmag21, 11月 2025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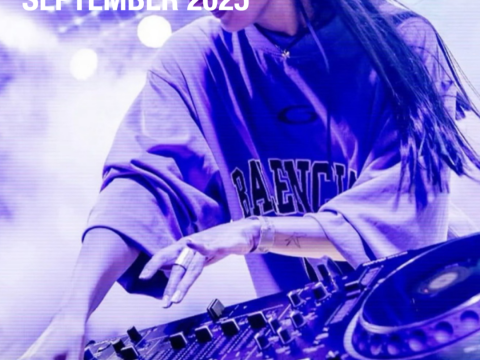
先锋DJ大赛|新老DJ在这里“打”成一片
Mixmag5, 9月 2025年
Buunshin: 感知速度,你需要先体验慢的感觉
Mixmag6, 6月 2024年
Louis The Child:现在可不是你挑食的时候
Mixmag27, 5月 2024年
Justice 从来都不是蠢朋克的接班人
Mixmag21, 5月 2024年


敬请留言
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