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DS: KAMILA RYMAJDO & JEMIMA SKALA
如果说跳舞音乐原来是种自给自足的乌托邦音乐,那么从2010年左右,它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有市场价值、甚至是可以贩卖给音乐场景以及派对人士的一种产品了。
随着这10年的发展,开始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从近几年的气候激进主义(climate activism)到安全空间政策(safe space polices)的兴起,还有那些在当地城镇中的主办方和厂牌,也全都在身体力行的积极改变现状。
在下面的列表中,我们汇编了11个主要趋势,看看这十年,跳舞音乐是怎么变得更加有道德感的。
来自南非的 DJ Black Coffee 之前表示,残障的艺术家可以登上音乐行业的最高殿堂。越来越多的音乐节也获得了类似 Attitude is Everything 等慈善组织的残障者保护认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残障人士能更方便地玩儿起来。
各种场馆也把关爱残障人士作为首要任务——比如曼彻斯特的 YES Space 就在2018年推出了“轮椅无障碍”政策,直接让它们从英国各种大大小小的艺术空间中脱颖而出。YES Space 还举办了一系列例如“Under One Roof”这种迎合有学习障碍人士的活动。上个月,伦敦还办了场史上第一个残障人士专属锐舞派对。
但从今年的 Manchester’s Pride(曼彻斯特一年一度的LGBT人群节日和游行)结束后,人们发现,关爱残障人士的种种努力其实还是挺失败的,因为在这种一次性的户外活动中,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措施来保证残障人士的出行方便和安全。
尽管有些 nightclub 在场地里修建坡道或者安装升降机,但在大多数市中心的场所里,根本没有残疾人专用停车位,很少有对轮椅用户友好的吧台,残疾人专用洗手间也几乎找不着。建筑更现代一些的国家情况稍微好一点。2016年搬到深圳的 DJ Katie Cooper 说:“在中国,其实很多顶尖的 nightclub 都很现代化,都有电梯供有需要的人使用。”
从曼彻斯特的 Techno 组织 Meat Free 之前实施的“你感觉这场演出值多少你就出多少钱门票”政策,再到波兰电子音乐节 Up To Date 推出的为失业者和50岁以上人群免门票计划,还有类似 Party For The People 这种通过网络售票为慈善机构和社会项目捐款的活动……具有道德感的售票方式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也开始让俱乐部和音乐节被所有人更好的接受。
然而,来自英国格拉斯哥俱乐部 FUSE 的老板 Sofya Staune 却说,实施这种政策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在我作为主办方的实践中来说,我曾试图为那些因任何原因负不起门票的人降价,但之前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的措辞,我一直尽量用广义的词来表达。但是我发现,如果想让大家接受这个提议,除非主办方不要求他们说明缺乏资金的原因。”
从 Disco 起源于黑人酷儿群体,到公然挑衅政府权威构建了英国的锐舞文化。跳舞音乐始终都是有政治性质的。
在2010年代,这种政治性更加明显。这十年中,财政紧缩被视为一种可行的政治策略时,“右派”成为了新纳粹分子更加友好的一种称呼,还有川普,英国退出欧盟这乱七八糟的破事,我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彻夜狂舞什么也不想,或者去做点什么。很多DJ开始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比如 Patrick Topping 和 Floating Points,他们在2017英国大选活动中参加了工党的集会,还有 R3 Soundsystem 组织的反对党派领导人的快闪活动。
来自利兹的派对厂牌“Puddles”也是个一边跳舞一边搞事情的例子。Puddles 是由 Lydia Lloyd-Henry、Jimmy Caldwell 和 Callum Walton 在 2016 年成立的,差不多是 2017 年夏天大选临近时。他们第一个活动就颇有政治意味——如果你在门口出示投票卡并且鼓励年轻人登记投票,就可以免费入场。虽然 Puddles 一直都把每一期都把利润捐给慈善机构,但 Lydia 说这一次是不同的。“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提醒我们自己,派对是可以帮助别人的。”
Callum 指出,正是因为许多 club 的倒闭,才促成了这个趋势:“这意味着许多新的派对,包括 Puddles,都诞生在小容量的DIY空间中,这让更多具有政治优势的派对成为一种可能。”
James 是一个派对爱好者,他说,跳舞音乐就是团队建设,整合政治目的然后建立成员,就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改变。James 说:“我认为在俱乐部里,你可以在瞬间迷失自我,这有助于你与周围的人和想法产生联系。没有这些联系政治运动就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不一定非得是舞曲,我认为它可以成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力量,能够保持政治运动的强大,帮助他们在进步中成长。”
这种明显有政治倾向派对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今年春天,英国各地掀起了一场以慈善为中心的活动,其中包括 Cosmic Slop,它成功筹集到240万英镑,通过比如 DJ Bone 等艺术家的工作以及一些类似 London’s The Cause 慈善场地的开幕,一起把利兹的某个铸造厂改造为一个多功能教育中心。
Room For Rebellion 是一个横跨伦敦、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俱乐部之夜,他们为北爱尔兰刚刚被推翻的古老堕胎法筹集资金并唤起人们的意识。联合创始人 Isis O’Regan 和 Anna Cafolla 受到 Savita Halappanavar 和 Ashleigh Topley 等一些人的启发,创造了一种“参与比疏远更好”的行动主义。Isis 解释说:“这是一个机会,利用我们的行动主义,创建一个志同道合的社区,反对父权制国家,建立一个支持网络,可以大胆阐明人身自主权和选择权,并以一种令人振奋的方式,带着使命的rave会让人更爽!”
由于议会最近通过了修正案,从10月21日起,堕胎在北爱尔兰现在是安全和合法的。Anna 说这并不意味着 Room For Rebellion 现在就是多余的了。“我认为我们和其他积极分子应该继续就生殖权利问题进行开放和包容的讨论,无论这种对话在哪里出现。跳舞音乐中的行动主义只会变得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性,更容易接近,我们都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为世界做贡献。”
“到2009年,看到女性站在俱乐部和音乐节上演出并不罕见。” DJ Paulette说,她1980年在曼彻斯特超级俱乐部 The Haçienda 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事业,是 The Haçienda 第一位女性常驻 DJ。“Amy Thompson 那时候负责 Swedish House Mafia 的运营,Caroline Protheroe 管理着 David Guetta 和 Olga Zeggers,Tomorrowland 那时候也快开了,正在装修。同时,Emily Eavis 掌管着 Glastonbury。10年后,女人们还在做这些事,但不用藏着掖着了。女性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声音,可以大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过自己的生活,无畏地谈论两性薪酬平等、权利、问题、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性。”
来自莫斯科的 A.Fruit 经营着 Get High On Bass 的俱乐部之夜,并且和 Worst Behavior 的 Anna Morgan 还有 Bell Curve 等人一起举办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活动。她说:“近几年我确实看到了越来越多对女性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在音乐制作和 DJ 之外工作的女性,比如经营唱片公司、电台节目还有派对主办方等等,她们都得到了认可。”但是,A.Fruit 说,至少在俄罗斯,“在像 techno 这样的大场景中,它发展的似乎更快。”在未来的十年里,仍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年龄歧视,与男性相比,很少有50岁以上的女性经常在大俱乐部里放歌。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男女平等阵容这说法刚刚得到关注。”SLUT DROP 的创始人 TACAT 说。2014年2月,他的俱乐部之夜在利兹启动。“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接受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但是我迫不及待要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代表,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不必’尝试’寻找艺术家来平衡这笔费用。”同时,波兰的 Oramics 在8月份撰写了一份支持 LGBTQI+组织团结起来的报告,把波兰对边缘化群体的暴力行为公之于众。
“在波兰独立俱乐部和各种音乐节中,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全球都在努力的事情,像 Primavera 这样的音乐节或者像曼彻斯特的 Cotton 俱乐部,都会优先考虑性别还有 LGBTQI+平衡阵容。但在波兰这样的民粹主义右翼政府掌权的国家,却越来越难了。“我们还有4年的时间(最近的议会选举增加了法律和司法的投票),他们已经接管了我们所有的文化机构和资金,”Oramics 的 FOQL 说。“但不知为何,它让我们更开放,更有创造力,它给了我们抵抗的力量。”
在过去的十年里,跳舞音乐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无疑对商业有利,但其主流吸引力的激增也引发了“更安全的空间”政策的扩散,这些政策也在重申包容和尊重的必要性。在英国和海外,像 “Love Muscle”、“Pxssy Palace”和“Equaliser”这样的派对团体一直在要求尊重和容忍,反对俱乐部中的性别、种族和性歧视,不管是让女孩还是少数群体,都可以安全不受侵犯的玩乐。
毕竟,在 Disco 和早期 House 的时代,现代舞曲是在黑人、同性恋者和其他边缘化人群的俱乐部里作为一种反抗的表达而诞生的。然而,这种抵制和反抗,却在没完没了的市场化和对俱乐部文化的粉饰中遭到了损害。
但我们应该感谢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团体站出来反对这种做法。德里的 Coven Code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们是一个经常被敌视的女性和第三性别者(non-binary )团体。“边缘化人群往往被抛弃,能够举办派对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个自由舒适的空间去享受生活。我们还认为,集体的真正力量在于不断努力寻找解决超越性别歧视的结构性问题的办法。”
像 Shambala 这样的独立音乐节多年来一直是环保的领导者,2016年他们就实行全素餐了。到了2019年,全行业的活动都开始考虑这件事了——英国独立节庆协会(AIF)呼吁禁止使用一次性帐篷,Glastonbury 音乐节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瓶。但是,俱乐部这么做的好像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唯一可见的变化是用纸质吸管代替塑料吸管。
就像 Tht Warehouse Project 的 Sacha Lord 说:“作为经营者,我们都必须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方面尽自己的一份力。Tht Warehouse Project 和 Parklife 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他告诉 Mixmag,“在新的 Mayfield Depot venue 中,用罐头和纸杯代替塑料,这样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回收再利用,这意味着有15万个塑料杯已经不会再出现了。通过大家一起努力,我们都可以为这个星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还有 Tail & Twis 的 ECODISCO,伦敦第一个消除所有一次性塑料杯的派对组织。组织者 Billy Mackie 和 Hadi Ahmadzadeh 今年在伦敦的 Oval Space 举办了他们的发布派对,随后,Oval Space 和 Pickle Factory 都从他们未来的活动中移除了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在他们未来几年的计划中,他们还打算和 Oval Space 还有生态慈善组织Worldrise合作,用火车和巴士在欧洲巡演,减少 DJ 们对欧洲短途航班的依赖。
类似 Extinction Rebellio,Greta Thunberg 和 Xiuhtezcatl Martinez 这种气候活动家近年来动摇了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他们鼓励我们重新思考消费主义,认真对待气候危机。跳舞音乐行业也被要求重新定制 party 的方式,希望能用一种更加环保的方式来狂欢。
Chal Ravens 是一名自由记者,也是 Clean Scene 的创始人。Clean Scene 是去年成立的一个特设组织,目前正在致力于怎么让跳舞音乐工作者们更容易环保。Clean Scene 的目的很简单:“我们只是想看到人们了解这个问题到底有多现实。”
一位已经明确表明过立场的 DJ 是 Hessle Audio 的 Joe,他自2014年开始就从来没有乘飞机去演过出——去年,他在奥地利林茨参加了一个音乐节,花了16个小时坐火车去那里。Jeo 很清楚,他并不是直接拒绝去参加距离很远的演出,如果有合适的,他可能还是会飞过去。但如果是欧洲之间的短途旅行,他肯定会选择更环保的方式,我们总是有机会做几件小事来创造更大的积极影响。Jeo 说:“气候行动是每个人的工作,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
为了严肃对待气候危机,Chal 和 Joe 都清楚地知道,花时间经营本地的文化场景,比让大牌 DJ 周末飞过来靠谱多了。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谈论心理健康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极度公开、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在几十年前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这财政紧缩的十年间,这种开放度的增加由于精神健康服务的削减而变得不平衡,病人看病经常要等好几个月。
在跳舞音乐行业,鉴于这种狂欢文化往往与心理健康的建议背道而驰(比如有睡眠的充足,不吸毒,让自己得到放松),心理健康绝对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像 Benga,Marie Davidson,Hot Since 82,Courtesy 和 James Blake 这样的艺术家都公开谈论了如何应对抑郁,焦虑和重度聚会。还建立了“The Mind Map”这样的在线门户网站,以为陷入困境的音乐年轻人提供支持。
对于某些人而言,参加派对彻夜跳舞甚至是有益的。Leah 告诉 Mixmag,她患有焦虑症而且很自卑,去俱乐部对她来说并没有加重病情,甚至是一种治疗手段。她说:“出去玩是一种释放,在有关心理健康的讨论中,自我照顾的那些建议是最基本的没用的屁话:睡个美容觉!保湿!多吃点该死的扁豆!但是自我照顾要比这些复杂多了——可以是出去和你最好的朋友鬼混。这是一种自我照顾的形式,因为它是一种与人交流的温暖感。”
为了使这种体验更具普遍性,Leah 意识到,在跳舞音乐行业中某些事情需要成为标配。她列举了更安全的空间政策(safer spaces policies),清醒的俱乐部之夜(sober club nights)和休闲室(chill-out rooms),以此作为发起人可以帮助他们的活动更加注意那些在晚上外出困难的人。
Leah 说,从本质上讲,在充满人的房间里像疯狂的跳舞,这也是一种体育锻炼。“事实证明,跳舞可以改善人的心理健康。”漫长的一周工作结束后,跳舞就不只是运动了,还可以释放各种压力。“人们开始意识到,放松下来到底有多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它作为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继续无休止的向外扩展舞蹈音乐产业,让它变得没有个性,变得商业,变得金钱至上,那么也许舞蹈音乐就会被视为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了。
在这篇文章中,Mixmag 的许多对话中出现的一件事是,在鼓励边缘群体的人们作为 DJ 和制作人参与方面,音乐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有多大。Chal 为《FACT》杂志撰写了一份定期的月度特辑,其中她挑选了最好的组合:“我他妈的一直在努力找一个白人直男!太疯狂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涌现出了许多技能分享网络社区,鼓励边缘社会群体扩大他们的知识基础,并参与到电子音乐的世界中去。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 Equaliser 和 Future Female Sounds,还有 Producergirls, 这是一个向妇女和性少数群体传授制作软件基础知识的学习班。
Tia Korpe 在哥本哈根创建了 Future Female Sounds 以作为人才的孵化器,她说,这是一种培养还未被发现的天赋并消除恐惧障碍的方法,支持和社区建设是这些技能分享空间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正如 Zoe 的 Equaliser 所描述的,“舞蹈音乐不应该完全关注于更新当前的场景使其更具包容性,而应该创造属于我们的新事物。”
这些空间的广泛成功是因为 Producergirls 的 EMMA 的不断努力,Producergirls 刚开始的时候正是 Boiler Room 的时代,女 DJ 们会因为她们的外表而在网络上受到抨击。技能分享网络社区在消除这种行为方面发挥了作用,“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空间都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了,” EMMA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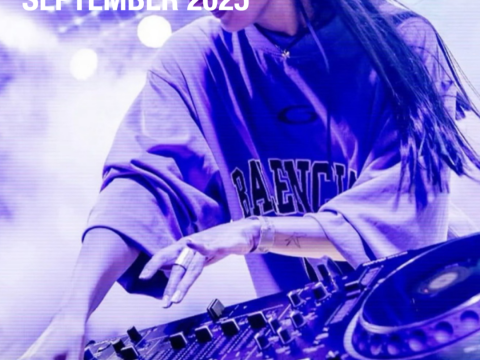






敬请留言
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