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之城底特律。Motown、Techno、Eminem 和 The White Stripes 的故乡,对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
在人才济济的底特律,有一位音乐人脱颖而出,如故事主线般贯穿了这个城市过去 30 多年的音乐历史:Joseph ‘Amp’ Fiddler。
除了自身的音乐造诣,Amp Fiddler 也影响了很多音乐人。早年的他曾作为键盘手活跃于 Funk 大师 George Clinton 所组建的 Parliament-Funkadelic 乐队。人们也津津乐道他和 Moodymann 两人惺惺相惜的友谊,以及他和 J Dilla 之间的师徒情谊。J Dilla 能够获得今日的成就,作为恩师的 Amp Fiddler 功不可没,是他教会了初出茅庐的 J Dilla 用采样器。
经历了生活的波澜起伏和人生的大起大落后,这位 Funk 元老和我们分享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
在底特律的成长经历
我记事以来最早的回忆之一是 67 年底特律暴乱期间,看着一辆辆坦克从我家门口开过。这并不可怕,相反的,那是我第一次骄傲的意识到,我们有黑豹(Black Panthers)这样的领袖们,可以自信得代表黑人群体为平等权益而抗争。
我姐姐是个嬉皮士,她带着一群黑豹组织的朋友回家。当时我还年幼,没有能力参与革命——我是 5 个孩子中最小的,对枪支和自卫一无所知——但这些身着黑豹制服的黑人同胞们的鼓舞了年幼的我。
我记得缠着妈妈出门给我去买了一套黑豹制服:一顶黑豹标志的贝雷帽、一件黑色套头衫、一件牛仔夹克和牛仔裤。
1967年后的社会变化
尽管美国已经迎来过了黑人总统,但真正的平等自由依然在路上,抗争远还未结束。警察依然在伤害着孩子们,杀人犯们仍然逍遥法外。这就是现实,荒谬而残酷。
即使如此,我依然对未来保持乐观。我相信终会有一天,人们不再以貌取人。

和音乐一同成长
我出生时,家里有一架小型三角钢琴。高中时,我妈给我报了钢琴课。但我当时非常讨厌上钢琴课,也不喜欢那个钢琴老师。直到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去底特律的 Grinnell 兄弟音乐商店。
当时底特律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算是个音乐人,我朋友是个吉他手,我们总是在地下室和车库里捣鼓音乐。我们本来的计划是去那儿偷东西,但我告诉朋友:“今天我不打算偷任何踏板。”
在店里,我和一位教钢琴的老妇人聊了起来,跟她报名学钢琴。我依然记得她的称呼是惠特尼小姐,当时大概 84 岁,课程的价格是半小时七美元。
我和音乐的不解之缘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和George Clinton共事
George 这家伙太棒了!他也是我最敬仰的音乐英雄。每个底特律的 Funk 音乐人的终极梦想都是去看 Parliament-Funkadelic 的现场。
我一直是 Funk 死忠粉,当时也开始尝试制作音乐。我女朋友把我的录音带给了 George,他听后很喜欢,希望我能回底特律和他一起做音乐。那时我在郊区一家叫做 Incognito 的独立商店工作,Incognito 主营另类服饰和摩登玩意儿,是底特律第一家卖 Dr. Martens 的商店。
我记得和 George 课程结束后,有人拿了张支票到商店里。我把支票从给了店主,他激动地大喊:“这真是太疯狂了!一张 George Clinton 的支票!”,然后叫妻子过来看一看。George 一伙人在 Incognito 里放了很多很酷的音乐,让我大开耳界,包括像 Cocteau Twins 这样的Alternative。
我和 George 一起在加利福尼亚住过一段时间,期间我受益匪浅。从音乐文化到人生哲学,George 教了我很多东西,包括让不爱读书的我爱上文学。他激励我勇于尝试,并对各种事物予以关注,这比呆在酒店房间里无所事事好多了。

教 J Dilla 使用采样器
我第一次见到 J Dilla 时,他就展露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
在以 Slam Village 名声大噪前,他曾是一个叫 Ghost Town 的音乐组织中的一员。有一天,这群年轻人找上门来,说想跟我学做音乐。我当时刚用第一笔预付款购置了一批音乐设备,包括一个 AkaiMPC60 采样器。估计他们是循着我地下室传出来的音乐声找到的我,毕竟捣鼓音乐挺大声的!他们跟我说:“你是制作人,我们会说唱……你能教我们吗?”我让他们明天来我家找我。
他们是一群很酷的孩子,我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来捣乱的。我跟他们说:“你们之中得有人需要学会如何使用这些设备,有人得做节拍。毕竟我没这么多时间管你们。”
他们决定说:“好呗,Dilla(Yancey, 也就是J Dilla)可以做节拍,他是我们中负责做这个的。”他此前已经在尝试用录音带作曲了,且天资过人——能在一首曲子中编入五六个不同的循环(Loop)可不简单。
我把他们接入了采样器,告诉他们该如何操作。Dilla 学的很认真,全程目不转睛。我只教了一次,Dilla 就搞懂了的主歌和副歌间的区别。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弄明白的。从那一刻起我就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孩子非同小可。
Dilla 每天都会来我家学做音乐,勤勉好学的他进步飞速。我期待有朝一日,底特律 Hip-Hop 能发扬光大,我在 Dilla 身上看到了希望。
友人 Kenny ‘Moodymann’ Dixon Jr
我伦敦厂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个叫 Moodymann 的家伙在底特律,让我一定要要见见他。我只是说:“再说吧!”我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是谁,最多四处打听一番。
有一天,我和歌手兼萨克斯手 NormaJean Bell 一伙人在工作室里做音乐,我和兄弟 Bubz(一个贝斯手)参与制作了他新专辑中的几首曲子。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叫 Kenny 的家伙。结束后,我们跟Kenny去了他的工作室,和他练一会儿。我看到房间里有张 Moodymann 的录音带,就问他:“你在帮这个人做音乐么?”他回答说:“不是啦,我就是 Moodymann。”
那是 2003 年前后,我正为自己首张专辑《Waltz Of The Ghetto Fly》找几首曲子。Kenny 有自己独特的制作风格:粗犷而天然,但让我联想到 George Clinton。从那以后,我就和他成为了挚友。
我们刚刚拍完了我的单曲《Return Of The Ghetto Fly》的 MV,结尾部分是我俩在底特律的溜冰场里溜冰!

遭遇创伤
我的家人们都一个个离我而去了。我遭遇了失去双亲的痛彻心扉,以及比这更糟的丧子之痛。
我在世上最亲的人是我的儿子,其次是我的母亲。第一个是我的父亲,他在 70 年代去世了。其次是我的母亲,她在 2006 年离开了。接下来,我的儿子 Dorian 因糖尿病并发症英年早逝,这件事对我打击沉重。
接着,我又在 2012 年送别了我姐姐,在 2016 年失去了我的兄弟 Bubz。我活的浑浑噩噩,根本无法从这一连串的惨剧中振作起来。
音乐人们邀请我为歌曲献声,我根本没有心思。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们给予我支持,我很可能无法从这段黑暗时光中振作起来。比如 Kenny,是他支撑着我制作了新专辑《AmpDog Knights》,并在他的厂牌 Mahogani 下发行。
学习组装钢琴
我正在学习如何组装钢琴。几周前,我把一台小型三角钢琴拆开,换了新的琴键,琴弦和击弦板,再重新装回去。现在还差一点就要完工了,我打算回底特律之后把剩下的最后一根琴弦装好,然后就可以开始练习了。
做这类事情可以让我保持积极性,但我在家制作音乐效率很低。
早年,家里总是热闹非凡:我儿子在地下室打鼓,我兄弟在楼上弹贝斯,我在中间一层弹钢琴。他们去世后,家里变得冷冰冰的、异常安静,这种感觉令我绝望。忧郁症的旋涡正在吞噬我,我得要找点人来我家陪我。
关于Donald Trump
我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做出更好的决定。这是我唯一能够说的。我不赞成他现在所做的决定,我只能期望他可以变好,就这样。
我的 Ghetto Fly 风格
在童年时,我总是会坐在门廊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其中有不少人从衣着打扮到走路姿势都十分有型。
很多年后,我在纽约看到一个家伙,和我记忆中那群人一摸一样。那时候,这群人被叫做“pimping”。他们有着独特的走路姿势,看起来像是在跳华尔兹舞。这就是我首张专辑《Waltz Of A GhettoFly》的题目的灵感来源。

对服饰的热爱
我现在已经开始减缓购买衣服的频率了。我的衣服实在太多了。但就在今天早上,我在火车上看到了一个拿着哈罗德的包,穿着崭新皮鞋的男人。当时我就心想:“糟糕!我又该去逛哈罗德百货了。”
我的帽子供应商刚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叫 Otis Damon,在亚特兰大拥有自己的帽子品牌,他在制作 Ghetto Fly 式帽子方面可以说是一绝。我还认识一个曼彻斯特的服装设计师叫 Maurice Whittingham,他的设计深得我心。伦敦就更不用说了,每次去完伦敦我都濒临破产!
鼓励孩子学音乐
我儿子一直很想学音乐,我也鼓励他这样做。可惜现如今,很多学校不再将音乐囊括入教育体系里,孩子们成长过程中良好的音乐环境正在被剥夺。这点真的很糟糕。
我想开展一个音乐项目,教孩子们学音乐,让他们重获学习音乐的权利。
学音乐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艺术审美,对学习其他学术课程也有辅助作用,数学、英语……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音乐促进一切。
有关信仰
我不属于任何宗教,但我有信仰。我时常质问上帝,为什么我会沦落到今天的境遇?为什么我的家人们都离我而去?有时,现实让我万念俱灰,或许世界上根本没有上帝,不然他为何要这样对我?
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继续做音乐,这是我存在的意义和目的。
我只需要变得坚强,坚持信仰,继续做我该做的。
Edit by 1NT3RN
from Mixmag.net

有关文章

Mixmag|从街头到赛场:电子音乐竞技的历程
Mixmag21, 11月 2025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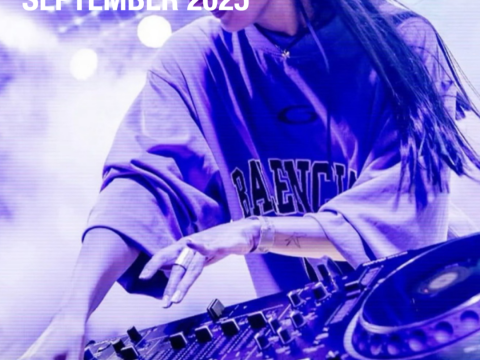
先锋DJ大赛|新老DJ在这里“打”成一片
Mixmag5, 9月 2025年
Buunshin: 感知速度,你需要先体验慢的感觉
Mixmag6, 6月 2024年
Louis The Child:现在可不是你挑食的时候
Mixmag27, 5月 2024年
Justice 从来都不是蠢朋克的接班人
Mixmag21, 5月 2024年


敬请留言
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