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电子音乐艺术家们正在远离他们之前所钟爱的俱乐部场景。
![]()
WORDS: ADÉLAÏDE DE CERJAT
2016年,法裔加拿大制作人 Marie Davidson 写了一首《Adieux Au Dancefloor》,坦率的法语歌词阐述了她对俱乐部场景的复杂感受——她说她完全迷失了,沉浸在绚烂又迷茫的夜生活中,忍受着巨大的孤独和焦虑,甚至说自己身处“地狱”。
三年后的 2019 年 8 月,她宣布从此完全放弃俱乐部演出。
她不是第一个离开俱乐部的艺术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一直和精神疾病作斗争的 Avcii 选择自杀之后,随着艺术家对自身心理健康和药物成瘾性的透明化,许多人敏锐地意识到典型的“DJ 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的风险。在之前 Mixmag 的推送文章中也报道了艺术家们关于在俱乐部中保持清醒的技巧,将参加活动的时间减到最少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方法。
比如来自 secretsundaze 厂牌的 Giles,他说:“如果你必须放完就回家也别感觉有什么不妥,你需要优先考虑自己。”还有来自 Abode 的发起人 Kai,他说:“不要在你上台前 3-4 小时就到达俱乐部,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然而,离开俱乐部的原因往往都是艺术性的,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在这个游戏中经历了数十年之久的人来说。Jeff Mills 经常对标准俱乐部 set 感到沮丧,从他的即兴爵士四重奏 Spiral Deluxe 到他的管弦乐队计划,他开创了将古典传统与电子音乐神奇融合的先河,这不仅揭示了他作品中的深度和艺术性,还向那些从来没有去过俱乐部的人展示了什么是 techno。
Jeff 不是唯一踏入管弦乐世界的底特律音乐先锋,当 Derrick May 去年推出了自己的管弦乐计划时,他说这不是关于要取代俱乐部环境,而是寻找一种音乐媒介,他一直想把这种媒介放在电影的范围内:“我做的每一件事,我创作的每一首歌,一直都能感觉到管弦乐队在里面。我喜欢把我的作品称之为’布景音乐’。那是带着点胜利野心的布景音乐。”天才 Carl Craig 是另一个这么做的艺术家,他在他的 Versus 项目中也充分构建了管弦乐的元素。
![]()
而且对于很多跨界艺术家来说,俱乐部并不是一个维度足够宽广到能表达他们所有想法的地方。Jessika Khazrik 拥有震撼全世界俱乐部所需要的所有 DJ 技术,而且还制作了比如《Mount Mound Refuse》之类的作品,这种声音和诗歌表演更多是在画廊或者活动空间中进行的。
Derrick May 认为,之前精英听众的民主化使人们得以进入这一新进程。“「管弦乐队的听众」一直以来都是那种非常高傲的客户,一个非常严谨的群体,他们只对享受过去感兴趣,并且会一直保持不变,他们知道这一点并且成为那个群体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享受自己是那其中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停留在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中期,现在不太出去看演出,也不会去音乐厅支持乐团了,这是管弦乐团开始接触电子音乐家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很多俱乐部场景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很多情况下,它不再是一个表达的场所,而是一个为 DJ 和艺术家设计的擂台,在这里,更宏大的表演和对制作的强调不仅会疏远人群,还会让 DJ 远离音乐,吞噬了俱乐部作为亚文化和抵抗之地的想法。
![]()
如果俱乐部的概念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对电子音乐的理解也会发生改变。随着各种流派的兴起,我们也被要求对音乐有着更高的接受度——比如 Simon Reynolds 在舞蹈音乐术语中最新添加的“Conceptronica”一词就描述了“music to contemplate with your ears, to think about and think with”(用耳朵去思考音乐)。
有这种思考感的“善于倾听的听众”很难聚集在一个俱乐部的混乱与兴奋之中。因此像 Actress,SOPHIE 甚至 DJ Koze 这样的艺术家们开始在音乐会场地中展示他们的音乐,还有注重聆听音乐的“听吧”(listening bar)的兴起。对此的回应也许是“俱乐部音乐”的传播,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流派,其根植于巴尔的摩和泽西岛等区域性场景,其原始形式的设计与舞池密不可分。
![]()
只听音乐不跳舞的“听吧”
许多音乐节和机构都试图在俱乐部文化的即时性和肉体性与“智慧性”方面找到一个中间地带。比如像 Sónar 和 Unsound 这样的先锋,还有 Dekmantel 将音乐节扩大到场外音乐会场,在那里你可以听到 SarahDavachi 或者 Deena Abdelwahed 之类的实验电子噪音。
当然,风险在于,如果我们离开了俱乐部空间,并将“高雅”的想法永久化,比如音乐会场地和艺术画廊,让舞曲合法化,那么我们的文化也会脱离其根源。俱乐部文化应该寻求改变这些制度,而不是改变自身以适应这些制度。我们不欠他们任何东西。
但是,只要有足够多的俱乐部保持真实,继续做亚文化的庇护所,创造爱、自豪感、自由和快乐,那我们就不会有问题。至于文章最前面提到的 Marie Davidson,她可能不再亲自现场表演了,但是她的音乐——比如那首 Mixmag 2019 的年度曲目《Work It》,她那极简主义又生气勃勃的 Soulwax 混音,确保她至少在精神上,还在为舞池工作。
// 翻译:uufu
编辑:J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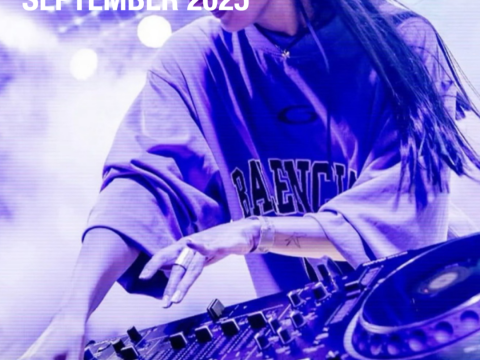






敬请留言
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